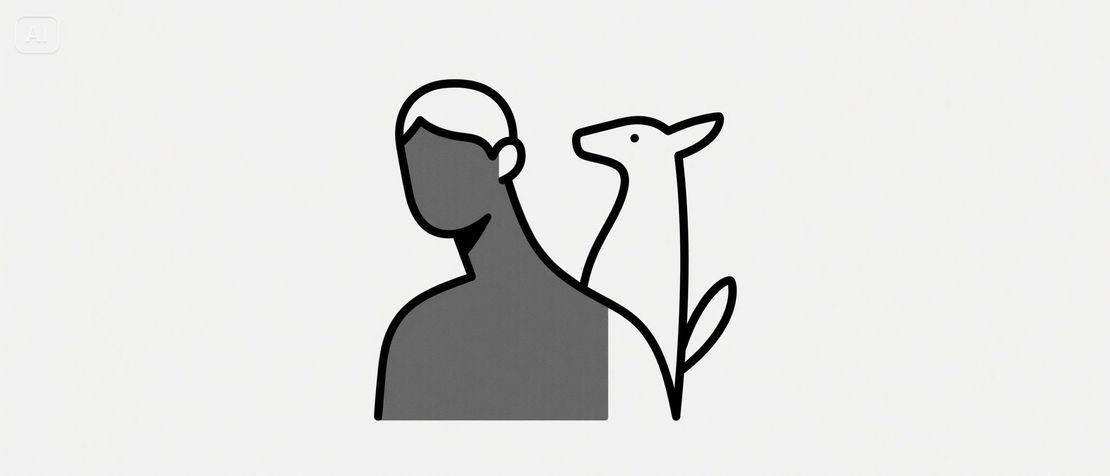理性的新引擎:我们应如何理解“人工智能+”的国家叙事
纵观人类文明的演进,其核心叙事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我们如何借助工具,挣脱自身心智的局限。
语言,让我们得以将稍纵即逝的思想固化为可共享的符号;文字与印刷术,则打破了记忆与知识在时空中的桎梏。
可以说,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都是为我们的大脑装配上一副更强大的“认知义肢”。
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正是这部宏大史诗的最新篇章。
然而,若仅仅将其解读为一份产业政策或技术蓝图,我们将错失其更为深远的意涵。
这份文件所描绘的,并非简单地为社会装上一个更快的“计算器”,而是启动一次深刻的、关乎整个社会认知操作系统的“范式重构”。
首先,我们需洞察“人工智能+”这一提法本身的精妙之处。它所强调的并非人工智能自身的精进,而是其作为一种赋能因子,与社会百业的广泛融合。
这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人工智能正从实验室中被仰望的“圣杯”,变为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水和电”。
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而是一个即将重写所有产业底层逻辑的“元能力”。这并非一次改良,而是一场“出埃及记”,引领我们走出旧有的生产与生活范式。
这份文件所昭示的第一个深刻变革,是信息创造权的解放。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创造新知识——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文化作品——都是人类心智独有的、甚至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特权。
而《意见》明确提出要“加速‘从0到1’重大科学发现进程”,并“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的内容。
这意味着,我们正将“发现”与“创造”的过程,从依赖少数天才灵光乍现的偶然,变为一种可被加速、可被规模化的“计算过程”。如同蒸汽机将人类从肌肉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样,人工智能正将我们从部分认知劳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信息的生产要素,首次历史性地加入了一个非人类的智慧实体。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变革,是信息产品的“液化”。
我们长久以来习惯的信息载体——文章、报告、书籍、视频——本质上都是一种“固态封装”。它们在发布的那一刻便凝固定格,以一种标准化的形态面对所有受众。
但《意见》中高频出现的“智能体”、“智能助理”等概念,预示着一个“液态信息”时代的到来。
未来的信息将不再是被动呈现的“展品”,而是主动服务的“管家”。它能根据你的身份、需求与场景,实时重组成最适合你的形态。我们与信息的关系,将从“阅读一份报纸”的单向接收,演变为“与一位博学的顾问对话”的双向探寻。
然而,理性的光芒总会投下悖论的阴影。当信息创造的成本趋近于零,当每个人都能借助AI轻易制造出看似无懈可击的文本与影像时,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便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如何确知什么是真实的?
信息的极大丰富,必然伴随着“事实”的通货膨胀与“信任”的空前稀缺。
这恰恰是《意见》最具远见之处。文件通篇贯穿着对“安全”、“治理”、“伦理”、“可信赖”的反复强调。这表明,国家顶层设计已经清晰地预见到,这场由技术驱动的认知革命,必须辅以一套稳健的社会契约与治理框架。
一个繁荣的智能社会,不能建立在真假莫辨的流沙之上。
而这,也正是我们媒体人必须面对的“斯芬克斯之问”。作为信息的专业处理者,我们曾经的价值建立在对“信息稀缺性”的掌控上。
如今,这条护城河已被AI的洪流彻底冲垮。我们的旧身份——信息的“生产者”与“把关人”——正在被解构。
但危机之中,新的使命正在浮现。
《意见》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当人人都能创造信息时,专业地“验证信息”便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媒体的未来,不在于和AI比拼内容生产的速度与数量,而在于成为这个喧嚣时代里“确定性”的供给者。
我们的产品,将不再是一篇篇报道,而是一项项“信任服务”——一个权威的事实核查中心、一个清晰的政策解读引擎、一个可靠的本地生活问答顾问。
《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远非一份寻常的政策文件。它是一份宣言,宣告了人机协同新纪元的开启;它也是一幅地图,勾勒出智能经济与智能社会的宏伟蓝图。
对我们媒体而言,它更像一次严峻的智力考验。我们能否放下对昔日荣光的眷恋,勇敢地拥抱一个被理性之光重塑的世界,将决定我们是被这场范式的洪流所淘汰,还是成为构建一个更智慧、更可信未来的中坚力量。
历史已经将理性的新引擎交到我们手中,而如何驾驭它,将定义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