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知重构:智能化浪潮下记者的“空心”焦虑与“再造”迷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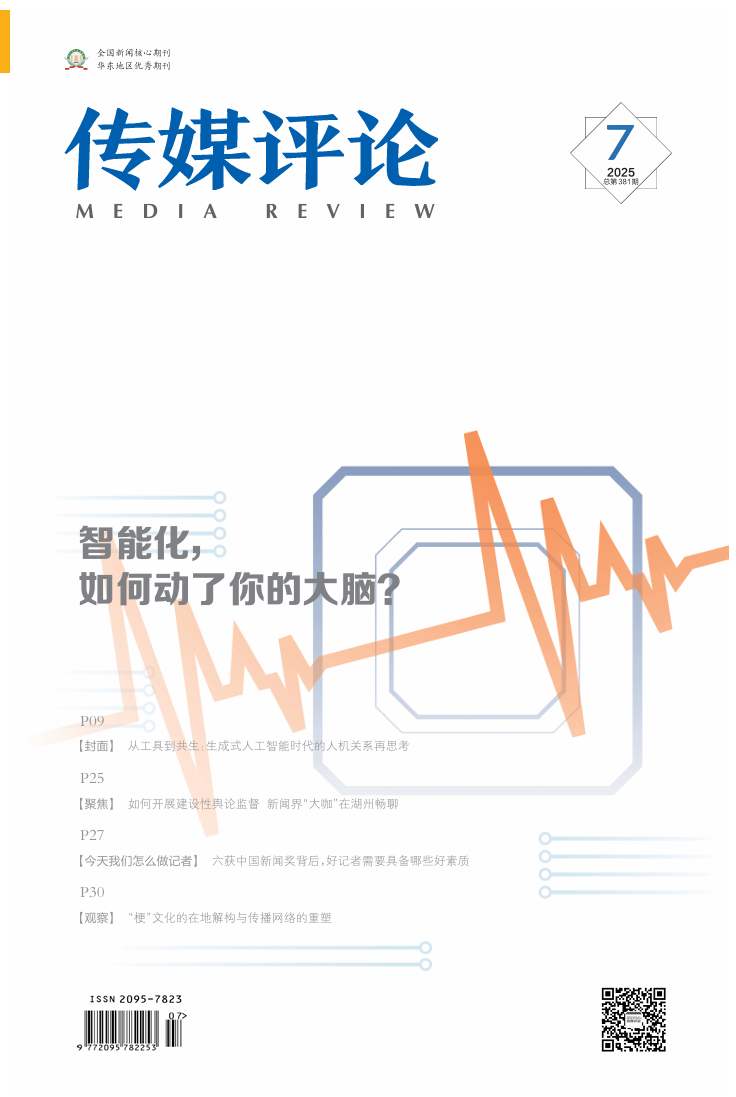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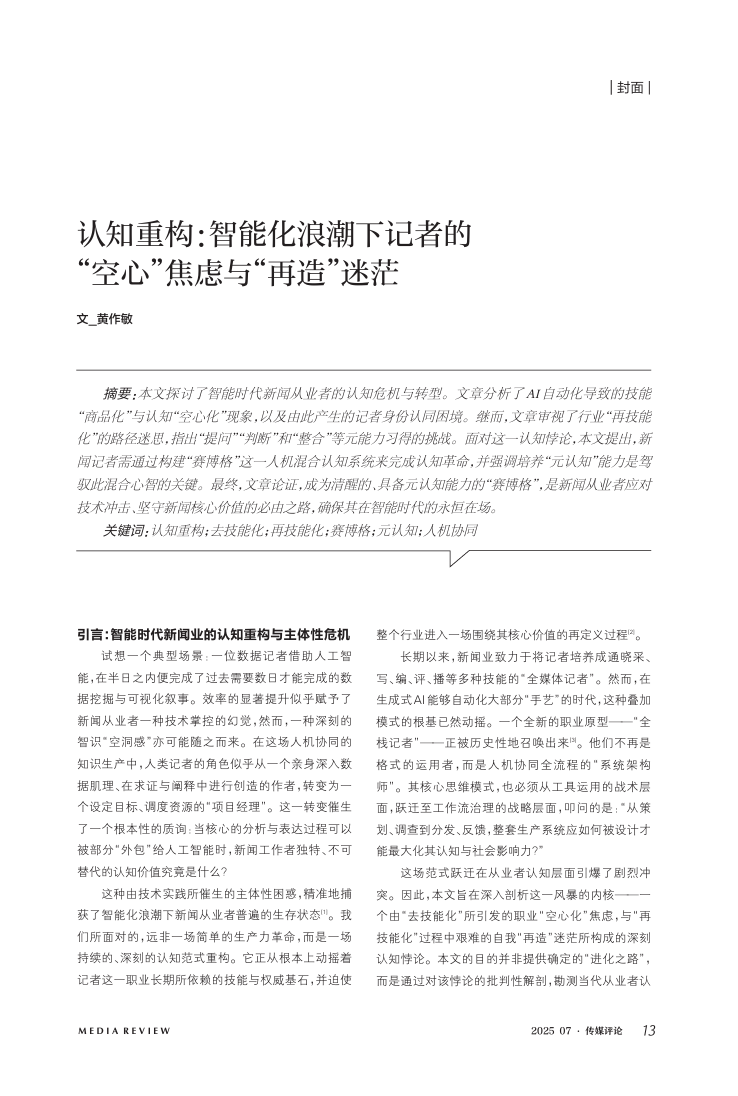
摘要
本文探讨了智能时代新闻从业者的认知危机与转型。文章分析了AI自动化导致的技能“商品化”与认知“空心化”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记者身份认同困境。继而,文章审视了行业“再技能化”的路径迷思,指出“提问”、“判断”和“整合”等元能力习得的挑战。 面对这一认知悖论,本文提出,新闻记者需通过构建“赛博格”这一人机混合认知系统来完成认知革命,并强调培养“元认知”能力是驾驭此混合心智的关键。最终,文章论证,成为清醒的、具备元认知能力的“赛博格”,是新闻从业者应对技术冲击、并坚守新闻核心价值的必由之路,确保其在智能时代的永恒在场。
关键词: 认知重构;去技能化;再技能化;赛博格;元认知;人机协同
引言:智能时代新闻业的认知重构与主体性危机
试想一个典型场景:一位数据记者借助人工智能,在半日之内便完成了过去需要数日才能完成的数据挖掘与可视化叙事。效率的显著提升似乎赋予了从业者一种技术掌控的幻觉,然而,一种深刻的智识“空洞感”亦可能随之而来。在这场人机协同的知识生产中,人类记者的角色似乎从一个亲身深入数据肌理、在求证与阐释中进行创造的作者,转变为一个设定目标、调度资源的“项目经理”。这一转变催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质询:当核心的分析与表达过程可以被部分“外包”给人工智能时,新闻工作者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认知价值究竟是什么?
这种由技术实践所催生的主体性困惑,精准地捕获了智能化浪潮下新闻从业者普遍的生存状态[1] 。我们所面对的,远非一场简单的生产力革命,而是一场持续的、深刻的认知范式重构。它正从根本上动摇着记者这一职业长期所依赖的技能与权威基石,并迫使整个行业进入一场围绕其核心价值的再定义过程[2] 。
长期以来,新闻业致力于将记者培养成通晓采、写、编、评、播等多种技能的“全媒体记者”。他们如同“瑞士军军刀”,其专业性的核心在于对不同媒介格式的熟练掌握与呈现[3] 。此范式根植于一种“工具箱思维”,其核心问题是“我该用哪种工具?”。然而,在生成式AI能够自动化大部分“手艺”的时代,这种叠加模式的根基已然动摇。一个全新的职业原型——“全栈记者”——正被历史性地召唤出来[4] 。他们不再是格式的运用者,而是人机协同全流程的“系统架构师”。其核心思维模式,也必须从工具运用的战术层面,跃迁至工作流治理的战略层面,叩问的是:“从策划、调查到分发、反馈,整套生产系统应如何被设计才能最大化其认知与社会影响力?”
这场范式跃迁在从业者认知层面引爆了剧烈冲突。因此,本文的核心论旨在于深入剖析这一风暴的内核——一个由“去技能化”所引发的职业“空心化”焦虑,与“再技能化”过程中艰难的自我“再造”迷茫所构成的深刻认知悖论。本文的目的并非提供确定的“进化之路”,而是旨在通过对该悖论的批判性解剖,勘测当代从业者认知重构的复杂地形,并揭示智能时代知识生产的权威、权责与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一、“去技能化”的幽灵:技艺的悬置与认知主体的危机
认知悖论的第一个层面,往往以一种技术赋能的积极面貌展开,其序曲通常是对效率的礼赞。然而,在这种由AI驱动的生产力飞跃背后,正上演着一场对传统新闻技艺的系统性悬置,以及对从业者认知模式的深刻改造。这构成了“去技能化”的第一个维度:一种弥散性的、关于专业价值被掏空的结构性焦虑。
1.1 技艺的商品化与“深度时间”的贬值
首先,AI对新闻业有形技能的自动化,正以一种不可逆的态势展开。信息检索、快速写作、事实核查、素材剪辑——这些曾构成行业专业壁垒的“看家本领”,正迅速地被商品化[7] 。它们从一种内嵌于记者个人经验、难以量化的专家知识,转变为一种可被标准流程批量复制、成本极低的外部服务。
然而,更深层次的危机潜藏于无形之中,它直接指向了新闻业最核心的认知过程——我们称之为“深度时间”的投入。这包括了沉浸于海量、甚至矛盾的资料中,通过反复比对、证伪与互搏,从而无限趋近事实真相的阐释性劳动;也包括了在与采访对象长期、互信的交往中,超越文本信息,捕捉其情感结构与微观语境的共情式探究。这些充满了不确定性、高度个人化且无法被量化考核的过程,恰恰是优质新闻报道之认识论深度与伦理厚度的基石。但在“一键生成”所代表的即时性、效率至上的逻辑面前,这种需要“慢火慢炖”的“深度时间”及其过程性价值,被系统性地悬置了。
1.2 认知卸载:心智“外包”的神经科学证据
对技术捷径的依赖,诱发了认知层面的范式转变,即认知科学中的“认知卸载”现象。此概念指涉个体将记忆、分析、归纳与决策等核心认知功能,系统性地委托给外部技术代理[5]。
此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2025年6月的一项研究,通过脑电图数据支持了这一现象[6] 。该研究将参与者分为“大型语言模型组”、“搜索引擎组”和“纯大脑”组进行论文写作任务,结果显示,随着外部支持的增加,大脑的神经连接性系统性降低。“纯大脑组”展现最强、最广泛的神经网络活动,而“大型语言模型组”的整体神经耦合最弱[6] 。
该研究进一步揭示,思考过程“外包”导致大脑核心心智功能因长期不使用而“萎缩”。长期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参与者,其大脑在Alpha频段(与内部注意力和语义处理相关)和Theta频段(与工作记忆和执行控制相关)的连接性显著低于“纯大脑组”[6] 。这表明,当写作无需依赖内部记忆提取和原创思维时,大脑相应的功能网络激活不足。
1.3 身份的“空心化”:从作者到“提示工程师”
至此,深层次的焦虑浮出水面——身份的“空心化”。当采写技艺被替代、思考过程被压缩时,新闻记者的专业独特性与存在价值面临根本性拷问。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从行为层面印证了这一危机:大型语言模型组的参与者在任务结束后,论文“所有权感”极低,且回忆自身论文内容时的引用能力与准确性显著受损。第一轮实验中,高达83.3%的大型语言模型使用者无法正确引用自己的文章,而“纯大脑组”的失败率仅为11.1%[6] 。
这种对自我本质的质疑,源于认知降级的恐惧。从业者担忧自身从主动的知识发现者与意义建构者,退化为人工智能系统的“提示工程师”或自动化内容的“质量监控员”。这种从生产链上游“作者”角色向下游辅助性、操作性角色的漂移,构成了对专业价值的真实拷问,亦是“去技能化”在新闻从业者精神世界投下的沉重阴影。
二、“再技能化”的迷思:悬浮于空中的元能力
面对“去技能化”的幽灵,行业话语迅速提出了“再技能化”的解决方案。这一论述敦促从业者放弃“贬值”的传统技艺,转而掌握人工智能难以取代的“元能力”,以攀登价值链顶端[8] 。然而,对多数一线工作者而言,这种看似明确的攀登指令,更像是技术乐观主义与人力资本焦虑共同构建的空中楼阁——其轮廓清晰,但通往路径却付之阙如。
2.1. 提问的技艺:从内容生产到议程设计
新话语体系中,从业者对人工智能的“战略性提问”能力备受推崇,被誉为新时代的“写作术”。其本质是从单纯的内容生产者转变为能够进行逻辑构建、目标拆解与议程设计的“对话架构师”[9]。
然而,这种能力的习得路径极度模糊。它并非一门可标准化传授的“科学”,而更接近一种依赖个人知识储备、领域洞察力与语感的“艺术”,深刻嵌入从业者既有文化资本与默会知识之中,难以剥离和量化教学。从业者被告知需“更好地提问”,却鲜有人能清晰界定“好问题”及系统达成方法。面对此困境,部分从业者自发探索适应性策略,如建立个人或团队“提示词资料库”,试图将此非结构化“艺术”部分转化为可复用、可迭代的实践模式,以在不确定探索中寻求确定性。
2.2. 判断的权力:算法黑箱的守门人
“再技能化”的第二个核心要求是发展“批判性判断力”,即“反思、质疑乃至审计AI”的能力,这使记者处于悖论境地。一方面,AI的“黑箱”运作机制对多数缺乏技术背景的从业者构成认知壁垒;另一方面,效率诱惑下,持续批判极难维持。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间接证实,大型语言模型可能加剧“回音室效应”,削弱使用者在算法强化单一视角下的批判意愿和能力[6]。
对此,从业者发展出“实践认识论”。例如,采用“对抗性验证法”,故意用矛盾或极端问题测试AI的逻辑与价值边界;更重要的是,在工作流中建立交叉验证机制,主动将AI输出降格为需要严格审查的匿名“初级信源”,而非终极答案。
2.3. 整合的重负:被迫成为“全栈知识人”
第三项元能力是“跨界整合力”,要求记者深度融合AI技术、垂直专业知识与新闻产品思维[10]。这使巨大的学习成本和认知负荷完全个体化,体现了新自由主义逻辑,即个人需对自身市场适应性负全责。从业者被迫成为永恒学习者,不断在广度与深度上自我投资以追赶技术迭代,承受巨大时间、精力与经济压力。对此,一种有效突围策略是“项目制学习”。从业者不再追求泛泛知识,而是专注于细分领域,在具体报道产品驱动下将AI作为实现目标的“杠杆”,在“做”中学,逐步构建独特“T型”知识结构。
结语:于悖论中进化——走向“赛博格”的自觉
经由前文对“去技能化”焦虑与“再技能化”迷思的双重剖析,一个根本性现实已然显现:新闻从业者所处的矛盾状态并非稍纵即逝的过渡阶段,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将长期存续的新常态[11] 。因此,走出困境的出路,不在于徒劳地寻求对立的消解,而在于完成一场更深层次的认知革命——即对“人”在技术环境中的主体身份,进行一次彻底的重估与再造。
3.1 新主体性的召唤:从孤立心智到“赛博格”
这条进化之路,要求我们拥抱并自觉地构建一个全新的职业身份——成为一名清醒的“赛博格”。此处的“赛博格”,并非指向生物与机械的物理融合,而是一种认识论与生存论层面的深刻转型。它借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洞见,意味着坦然承认:在智能时代,人类认知主体已不再是孤立、自主的“自然有机体”,而是已与AI这个强大的“外脑”深度共生,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机混合认知系统[12] 。
接受这一身份,意味着我们必须主动放弃对“纯粹人性”的怀旧式坚守,转而思考如何治理这个人机混合体。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为这一必要性提供了神经科学层面的佐证:无节制地依赖外部智能,会导致大脑关键网络(如Alpha和Theta频段)连接性减弱,并累积起长期的“认知债务”[5] [6] 。而“赛博格”的自觉,恰恰是对这种认知风险的主动回应。
在这种新模式下,人机分工将被重新界定:AI被策略性地部署于处理规模化的信息搜集、模式化的内容生成以及初步的事实比对;而人类记者则必须将认知资源聚焦于那些无法被算法轻易量化的、真正体现人之价值的环节——设定议程、提出独创性问题、实现关键性的采访突破、做出复杂的伦理权衡,并最终为报道注入人性的温度、同情与价值观的灵魂。
3.2 元认知:驾驭混合心智的核心能力
若要有效治理这个全新的“混合心智”,从业者最需培养的,是一种“元认知”的能力——即“关于思考的思考”。这才是智能化时代最高阶、也最核心的“再技能化”。它要求从业者从一个无意识的技术使用者,转变为一个对其自身与AI的认知过程,具备持续的自我监控、批判性反思与主动干预能力的“系统管理员”。
这种元认知能力并非空泛的理论,而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刻意实践来塑造:例如,建立“AI交互反思日志”,旨在系统性地复盘人机协作的得失;或在关键的创造性环节(如选题策划、核心论点提炼)设置“无AI思考区”,以此作为一种对抗“认知卸载”的策略,确保大脑核心的原创能力不被削弱;以及在团队层面组织“人机协作复盘会”,将个体零散的经验,转化为组织共享的知识与最佳实践。
3.3 前瞻性展望:新闻生态的演进与价值重申
这场由个体大脑内部认知重构所驱动的革命,必将深刻重塑整个新闻行业的未来生态。未来的媒体机构,其核心竞争力或许不再是内容生产的规模与速度,而是其人机协同系统的智慧与伦理鲁棒性。传统的部门划分可能被更具适应性的“项目制”敏捷团队所取代,同时,诸如“AI伦理官”、“计算传播师”等融合了技术、人文与新闻学识的新岗位亦将应运而生。这些新角色的职责,正是为整个组织的技术应用与价值坚守提供制度性保障。
最终,智能化“如何动了你的大脑”这一时代之问,其答案绝非宿命。从业者既可能在无意识中被技术“格式化”,沦为“认知降级”的牺牲品;也能够通过自觉的认知革命,主动对人机关系进行“再编程”。
通过成为清醒的、具备元认知能力的“赛博格”,我们在智能浪潮中要捍卫的,将不仅是一份职业的存续,更是新闻业作为社会瞭望者、意义阐释者与伦理守望者的核心价值与永恒在场。
(作者:黄作敏 温州新闻网副总编辑)
参考文献
[1] 胡晓娟, 朱海瑜, 陈欢, 等.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人的价值体认与再职业化[J]. 青年记者, 2023(21): 9-14.
[2] 王薇, 刘大椿. ChatGPT的进化与人的主体性[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24, 41(5): 22-29.
[3] 何耀军. “全能记者”的前世、今生、未来——媒体融合背景下记者的定位与发展[D]. 青海: 青海师范大学, 2023.
[4] 黄作敏. 对话框媒体: 一种未来的人机交互场景[J]. 传媒评论, 2023(06): 40-42.
[5] Gerlich M. AI Tools in Society: Impacts on Cognitive Offloading and the Future of Critical Thinking[J]. Societies, 2025, 15(1): 6. DOI: 10.3390/soc15010006.
[6] Kosmyna N, Hauptmann E, Yuan Y T, et al. Your Brain on ChatGPT: Accumulation of Cognitive Debt when Using an AI Assistant for Essay Writing Task[J/OL]. arXiv, 2025-06-10 [2025-06-10]. arXiv: 2506.08872. DOI: 10.48550/arXiv.2506.08872.
[7] 赵熙敏, 任志明.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记者的能力挑战与价值重塑[J]. 传媒, 2021(05): 41-43.
[8] 孙茜. 人工智能背景下新闻记者的能力挑战与价值重塑探讨[J]. 记者摇篮, 2025(01): 153-155.
[9] 魏江. 再塑培养体系[J]. 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 2024(5): 3-4. DOI: 10.3969/j.issn.1004-4892.2024.05.001.
[10] 何羿翯. 从AIGC生产探究全媒体生产方式变革[J]. 新闻世界, 2025(3): 10-13.
[11] 姜桐玲, 李若岩. AIGC在融合新闻报道中的“变”与“不变”——以近5年主流媒体全国两会融媒体报道为例[J]. 新闻论坛, 2024(3): 30-32.
[12] 孙珊. 唐娜·哈拉维“赛博格”思想及其传播学意蕴研究[D]. 湖南: 湘潭大学, 2014. DOI: 10.7666/d.D588543.